資本總是追逐更高的利潤。作為上市公司,GQY、威創(chuàng)、彩訊自然明白這個(gè)道理。這些企業(yè)的管理層不僅要使得企業(yè)在傳統(tǒng)優(yōu)勢的DLP大屏業(yè)務(wù)上的“持續(xù)領(lǐng)先”,更要?jiǎng)?chuàng)造企業(yè)嶄新的價(jià)值點(diǎn),為投資者帶來“未來更多的希望”。但是,DLP大屏企業(yè)走出去并不容易。
首先,競爭無處不在。無論是彩訊的LED大屏、威創(chuàng)的中端LCD大屏、GQY的機(jī)器人行業(yè),都不僅僅是這些企業(yè)在競爭。甚至,LED大屏、LCD大屏市場都已經(jīng)是比較成熟的行業(yè),擁有著各自特殊的規(guī)律和產(chǎn)業(yè)結(jié)構(gòu)。比如LCD拼接大屏,就有三星/LG這樣的巨頭,很多國內(nèi)中小從業(yè)者,包括安防、商業(yè)顯示、彩電等不同行業(yè)的企業(yè)在“共同較量”:威創(chuàng)擁有LCD大屏和DLP大屏之間,顯示技術(shù)自然延伸、客戶群部分重疊的優(yōu)勢,但是,其它的LCD大屏行業(yè)的參與者也并非“一無是處”,甚至擁有更多的優(yōu)勢。
競爭的存在不僅僅在于DLP大屏企業(yè)走出去的新領(lǐng)域,也在于DLP大屏企業(yè)固有的優(yōu)勢市場:DLP拼接墻領(lǐng)域。比如傳統(tǒng)安防廠商海康威視有自主品牌的DLP拼接墻,部分影響了原有DLP大屏企業(yè)的客戶選擇;液晶和等離子拼接墻不斷向高端市場發(fā)力,搶占了部分DLP產(chǎn)品的份額;部分液晶和等離子拼接墻企業(yè)推出DLP拼接產(chǎn)品,和DLP大屏傳統(tǒng)巨頭一爭高下。
固有優(yōu)勢的DLP大屏市場并非鐵板一塊;DLP大屏企業(yè)走出去的新興領(lǐng)域也是競爭激烈。這可是前有狼后有虎的格局,在此行業(yè)背景下,誰又能穩(wěn)坐釣魚臺(tái),巋然不動(dòng)呢?
第二,未來存在不可知性。拿DLP拼接墻來講,激光光源會(huì)不會(huì)上演LED光源快速爆發(fā)的潮流呢?答案沒人知道。在更大的范圍內(nèi),LCD拼接墻最終會(huì)不會(huì)成為在主要性能上全面匹敵DLP的對手呢?OLED平板顯示會(huì)不會(huì)是拼接墻行業(yè)下一個(gè)黑馬技術(shù)呢?答案更無人可知。
這種對未來不確定性、不可知性的擔(dān)憂是普遍的。例如LED大屏市場已經(jīng)走入“后成長期”,面臨量增減緩、價(jià)降增速的瓶頸;GQY的安全機(jī)器人行業(yè)完全是一個(gè)新興產(chǎn)業(yè):產(chǎn)業(yè)應(yīng)用多長時(shí)間能成熟、多久能走出“投入期”、最終產(chǎn)業(yè)規(guī)模能做到多大,甚至GQY如何界定自己的“產(chǎn)品類型外沿”都是未知的事情。
因此,大屏行業(yè)的領(lǐng)頭羊需要不斷嘗試新的方法和產(chǎn)品、需要“不把雞蛋放在一個(gè)籃子里”——這些問題,不是創(chuàng)業(yè)期的企業(yè)所能遇到的。遇到這些問題,是企業(yè)進(jìn)入成熟成長階段的標(biāo)志,但是對于國內(nèi)DLP大屏行業(yè)的領(lǐng)頭羊而言,則是第一次遇到的“沒有經(jīng)驗(yàn)的問題”。
第三,誘惑太多,方向在哪里?現(xiàn)在,DLP大屏行業(yè)的領(lǐng)頭企業(yè)已經(jīng)完成行業(yè)的原始積累,他們有些資金、有些資源、有些力量、有些精力,做一些關(guān)于企業(yè)進(jìn)一步發(fā)展的課題了。但是,跨出去的腳,落在哪里是一個(gè)巨大的問題:GQY的機(jī)器人嗎、威創(chuàng)的LCD嗎、巴可的數(shù)字告示和中端投影嗎?
技術(shù)相關(guān)、行業(yè)相關(guān)、與原有客戶群重疊,這是DLP大屏企業(yè)選擇跨出去的目的地的“基本原則”。但是,就是符合這幾個(gè)原則的市場范圍,也不僅僅是三五個(gè),至少也有幾十個(gè)。自動(dòng)化產(chǎn)品、機(jī)器人產(chǎn)品、信息化設(shè)備、軟件系統(tǒng)、專用計(jì)算設(shè)備、安全相關(guān)、專用通信產(chǎn)品、工程顯示到商用甚至家用顯示、工程安全到商用或者家庭安全——誘惑太多了!太多的可能自然成為決策者的煩惱。
第四,以靜制動(dòng)已經(jīng)不合時(shí)宜。既然DLP大屏企業(yè)走出DLP圈很不容易,那么何不選擇以靜制動(dòng)、后發(fā)制人呢?答案是,競爭者不會(huì)給你“后發(fā)”的機(jī)會(huì)。
DLP大屏行業(yè)本質(zhì)是屬于信息化設(shè)備。信息化行業(yè)的特點(diǎn)是一個(gè)平臺(tái)、多個(gè)功能、綜合應(yīng)用。比如,最早的MP3播放機(jī)已經(jīng)消失,他的功能成為智能手機(jī)的一部分;漢王希望以電子書這種功能成就一種產(chǎn)品的輝煌,卻很快被淹沒到了智能手機(jī)和平板電腦的漩渦里:如果,還是孤立的看待DLP大屏顯示系統(tǒng)這種顯示功能的產(chǎn)品,那么就是自愿的將自己吊在懸崖的邊上。
因此,2013年威創(chuàng)提出大屏“生態(tài)”這個(gè)概念。著重在戰(zhàn)略上指明,固守DLP大屏顯示一種功能、一種應(yīng)用、一種產(chǎn)品,而不與信息化融合是沒有出路的。事實(shí)上,海康威視作為安防企業(yè)已經(jīng)在做DLP大屏,華平作為視頻會(huì)議和通信企業(yè)也在做電子白板:那種以靜制動(dòng)、后發(fā)制人者,只有一個(gè)前途——“被人家抄了后路”都不知道。
綜上所述,“跨出DLP大屏圈”對于DLP大屏企業(yè)既是主動(dòng)性的需求、也有客觀必然性。但是,延伸產(chǎn)業(yè)鏈,卻并非是簡單的復(fù)制原有的經(jīng)驗(yàn),而是根本的企業(yè)革命,是DLP大屏企業(yè)的“二次創(chuàng)業(y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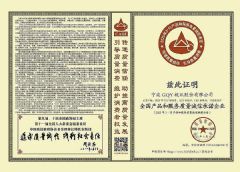




 Vtron威創(chuàng)拼接墻
Vtron威創(chuàng)拼接墻 臺(tái)達(dá)拼接墻
臺(tái)達(dá)拼接墻 飛利浦液晶拼接墻
飛利浦液晶拼接墻 aoc
aoc cisone啟沃
cisone啟沃 WAP手機(jī)版
WAP手機(jī)版 建議反饋
建議反饋 官方微博
官方微博 微信掃一掃
微信掃一掃 PjTime
PjTim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