盡管曾經一度輝煌,但由于商業環境的迅速改變,三洋正面臨一場前所未有的管理挑戰。從技術變革、產品競爭一直延伸到營銷、市場,再到組織架構及管理層危機,就像多米諾骨牌一樣一層層地向下倒去。
如果還記得,長虹的APEX事件,問題在倪潤峰時期已經存在,何以要等到趙勇上臺才得以深度暴露?很簡單,因為趙勇根本不想為倪潤峰的錯誤買單。
。
2007年2月23日,距離三洋電機2006財年結束的3月31日還差30余天,一場假賬風波開始在“三洋”的上空盤旋。
日本媒體(《朝日新聞》)披露:三洋涉嫌對2004財年中子公司的賬目進行粉飾,對子公司原本虧損的約1900億日元未能全部并賬,只在對外的財報披露中填寫了500億日元的虧損。
“這嚴重違反了日本的會計準則與信息披露的原則,三洋有可能重蹈安然事件的覆轍。”歐美媒體對此評論犀利。
安然的前車之鑒令人觸目驚心,“但是,應深入反思的是,有意為之的假賬行為是否就是平地波瀾,其背后是否隱藏更深刻的管理問題呢?”一位來自澳洲會計師公會的財務人員對記者說。
2004財年,正是三洋醞釀企業變革的時期,盡管曾經一度輝煌,但由于商業環境的迅速改變,三洋正面臨一場前所未有的管理挑戰。從技術變革、產品競爭一直延伸到營銷、市場,再到組織架構及管理層危機,就像多米諾骨牌一樣一層層地向下倒去。
“當時三洋的產品策略,區別于索尼、三星、松下等日韓企業的整機生產為主,主要提供更為基礎的關鍵零部件,如電視機機芯等產品。雖然涉及的產業領域相當廣泛,但實際上,三洋的核心產品仍在于其零部件的生產能力,一些整機的生產則通過合資公司完成。”一位曾經在三洋(中國)工作過的內部人士陸華(化名)告訴記者,“不過,在商業環境迅速變化的時代,當年缺乏研發能力,不得不向三洋購買機芯產品的索尼、東芝、三星們如今已經有了自己的替代產品,產業鏈向前延伸,三洋的大客戶們搖身一變成為了強勁的競爭對手。”
分析人員認為,在這個時候,三洋要做的,應該是反其道而行之,產業鏈由關鍵零部件向整機生產延伸,從而與競爭對手形成抗衡。事實上,三洋在近三年的企業變革中也在實踐這一目標,只是這場變革談何容易。
一旦涉及整機的生產與銷售,在這一轉型的背后,是三洋整個客戶市場策略的變革,關鍵零部件的客戶主要是行業客戶,而整機的客戶往往是最終消費者,由此,整個營銷策略包括渠道策略都要隨之改變。
然而,在整機的營銷渠道方面,三洋卻并不擅長,尤其是原有的企業結構大大阻礙了相關策略的實施。在2003年前后,壓力、阻力積蓄已久的三洋開始實施組織結構的變革,由事業部制轉為集團制,意味著三洋開始由“產品導向”向“客戶導向”轉移。
可悲的是,這場正確決策背后的“導向轉移”卻未能也不可能輻射到已經冉冉升起的中國市場。當時三洋在中國的發展,誠如三洋民用產品企業集團COO壽英司所說的,“三洋在中國國內形成的某些合資合作關系,不可能推倒重來。”
壽英司說這話的時候,正是2004財年結束的時候,當時的統計數字顯示,截至2003年,三洋共在中國14個城市設立42家工廠,共有合資與獨資公司13家。壽英司說:“很多合資公司中,三洋并不擁有主導權,即使在中國很成功,三洋也沒有決策的權力,調整起來非常困難。”
以當年頗受日方推崇的合作方華強、大冷、榮事達等企業為例,其內部的問題不勝枚舉。記者當年在采訪大冷股份(6.99,0.16,2.34%)時,其負責人曾向記者抱怨:“最早與三洋簽訂合作協議的時候,為打開市場,品牌與商標都用了三洋的,后來才知道品牌與商標的價值有多大,后期的合作就堅決避免了這種情況。”其利益博奕卻可見一斑。
在這種情況下,三洋的裹步難行恰恰給了競爭對手機會,索尼、三星們先走了一步。對比三星與三洋近幾年的財報,同樣可以看出,當前者借助中國市場獲得巨大飛躍的時候,三洋一半以上的銷售收入仍然來自日本本土市場。
如果技術不能滿足市場的需求,市場就不會收回足夠的可用于技術研發的資金,相對的,沒有新技術的開發,企業就會被市場遠遠甩在一邊。一向注重技術研發的三洋在市場萎縮,收入窘迫的情況下,也不得不陷入了技術與市場的惡性循環。這種循環,最終鎖定在了公司的經營業績上面。
按照三洋公布的2004年財報,三洋的凈收益是134億日元,每股收益7.2日元,每股現金分紅達6.0日元,每“美存托憑證”收益為36日元,現金分紅為30日元。
如果這份財報真得像《朝日新聞》所披露的那樣,有1400億日元的虧損沒有做并賬處理,那么,2004財年的凈收益就會成為一個巨大數字的凈虧損,股東收益與分紅也就會化為烏有,而管理層更是難辭其咎。
“我們有必要來看看三洋當年的股東結構與高管層背景,直到2004年的近半個世紀中,公司創辦人井植歲男(ToshioIue)家族一直保有對三洋的控制權,2004財年正值其子井植敏(SatoshiIue)擔任公司董事長,其孫井植敏雄擔任CEO的時候。”陸華說,“有可能在他們看來,1900億日元的虧損作并賬處理,那么三洋的‘股價’,‘管理人薪酬’,‘股票’,‘銀行貸款’,‘在上下游產業鏈中的信譽’都會受到巨大的負面影響,而且很可能破壞三洋醞釀已久的重組計劃,因而三洋寄希望于未來的企業變革,及變革后企業更高利潤對這筆虧損的沖銷。”
可以說,如果三洋的重組計劃很快在市場上獲得成功,三洋的假賬問題很可能會瞞天過海,就像許多渡過財務危機的企業曾經的做法一樣,三洋還是三洋。
然而,三洋的重組變革在短短的一兩年內收效甚微,產品銷售疲軟,經營業績欠佳,作為遮羞布被寄予厚望的“未來利潤”已然難以成形,2005年財年三洋的虧損達到1715億日元。
在這種情況下,井植敏力邀由記者出身的女董事野中知世接任CEO以轉移人們的視線,同時推舉自己的另一個兒子井植敏雅出任公司總裁兼首席運營官(COO)。
正如媒體當年預測的,在電子行業還算資歷很淺的野中知世根本難以扳回敗局,2006財年,三洋虧損更是達到2057億日元。
2006年2月8日,賬面已是“衣不蔽體”的三洋不得不向股東宣布,“實施增資計劃,吸收高盛集團、大和證券與住友三井金融集團集體注資3000億日元(25億美元),用于恢復財務健康,并推進結構變革。”
由此,三洋勉強渡過破產危機,但管理控制權也轉移給了這三大投資機構,為假賬的暴露準備了人事上的條件。
暴露假賬,新管理層有意而為之?
“注資后很快取得三洋管理控制權的高盛集團、大和證券與住友三井金融集團,都是馳騁全球資本市場數十年的老牌金融機構,而為什么在當年注資之前沒有審計出或者沒有披露出1900億日元的虧損呢?”來自方正投資的柳忠英女士分析說。
為什么在其注資完成后的第一個財年結束前,恰恰是這個時候,被粉飾過的1900億日元的虧損得以暴露出?是這些金融大鱷們不想為昔日井植家族的問題買單,還是另有其他的隱情?
或者,從三洋近一年來頻頻推出的治理舉措不難看出些端倪。
“增資計劃”宣稱,為改善三洋的財務狀況,加大研發力度,三洋在2006財年需要2200億日元的投資,2007財年需要2300億日元,而且,結構改革的加速和實施更是需要1000億日元,因而不得不引進金融集團的高達3000億日元的注資。
然而,與注資一同到達的,是對控制權的要求。2006年2月24日,三洋召開股東特別會議,簽署了注資后的公司章程,該章程規定:董事會成員由不多于15人減少為不多于9人,并縮短董事任期為1年。同時,為了使董事們更好地履行自己的職責,章程中也通過了這樣的條款:對董事責任的限制范圍在法律要求的幅度之內。
在上述的股東特別會議上,有7位董事會成員被重新推選,共有4位新的外部董事加入了董事會,兩位新董事來自于大和證券,另兩位新董事來自于高盛集團,管理控制權也由此發生變更。
隨后,高層管理結構也發生了重大變革。
2006年6月23日,三洋再次召開董事會會議,再次通過一項決議,在上述的外部董事中,兩位被再次推選,擔任董事會當天會議的執行董事。
為了保證董事會成員高效完成工作任務,公司決定,每月召開一次董事會,做出重要決策,并檢查董事們的事務執行情況。而且,三洋廢止了以往選任CEO,COO與CFO的體制,取消了基于該選任體制的頂層管理會議,取而代之的是一個由新管理成員組建的“籌劃指導委員會”,作為三洋的決策實體。
來自日本三洋全球總部的一位員工告訴記者:“該決策實體的成立,進一步加強了董事會對公司業務的控制。事實上,為了便于每次董事會會議都能夠深思熟慮和提升管理效率,所有董事會成員都要參加每月至少兩次的‘籌劃指導委員會’會議。”
可以說,這番舉措極大地加強了三洋的公司治理,但它還會產生一個副產品,就是對之前的假賬(如果假賬屬實的話)來說,以前的管理層再也捂不住了。
“新上任的班子絕對不會為之前的股東承擔假賬的責任,力量雙方一定經過了很長時間的博弈,最后一方決定暴露此事,他們按照其他跨國公司通常的做法,選擇在注資后第一個財年結束,也就是2007年3月31日到來這前找機會暴露進而撇清這件事情,因為到以后就沒有機會了。”相關分析人員說。
誰是真正的受益者?
此外,一個重要的事實是,假賬的曝出對高盛等三大金融機構是有好處的,主要有以下幾種可能:
第一,假賬曝出后,股價勢必受到打壓,高盛們可以借機低價吸進股份;第二,如果虧損屬實,高盛在注資前的資產就要縮水,那么相對的,3000億日元注資所占的股份就提高了;第三,假賬問題一旦屬實,為挽救三洋在公眾投資者心目中的信心,井植家族很可能被迫轉讓或者釋放相當的股份,這樣這些金融大鱷們就有機會優先購買。
這似乎與三洋的家族企業變革有關,家族企業往往疏于公司治理,商業環境一旦改變,或者家族企業尋求做大,勢必要引進機構投資,這時候,玩資本于股掌的金融大鱷們會用有超越我們想象的策略與方式來吸進股份,或者賺取資本游戲背后的巨額利潤。
三洋假賬案被媒體披露之后的當日,三洋在自己的官方網站上承認了正在配合日本證券監督管理委員會的調查,但同時表示不方便就此發表任何看法。
記者通過一個駐日本的朋友了解到,目前,針對媒體將三洋比擬成“第二個安然”,很多日本消費者并不以為然,他們認為三洋不會倒閉。從三洋在日本本土近50%的銷售比重來看,這似乎對三洋是一個很大的支持。
當然,三洋近幾年在管理變革方面的勵精圖治,及其所取得的成就,使投資者也仍然對三洋保有期待。
陸華告訴記者:“2005年11月,三洋推出了旨在進行內外部變革的‘中期管理計劃’,該計劃著力于打破三洋傳統的消費電子生產商的形象,塑造一個領先的基于環境與能源相關產品與服務的提供商。”
“同時三洋的業務被一分為二,一部分為核心業務,包括能源解決方案、HVAC產品與商業設備業務,個人移動設備業務;另一部分為亟須進行結構變革的業務,包括半導體、AV設備、家庭器具、財務服務。當然,三洋宣布將集中更多的管理資源在核心業務層面。”
中期管理計劃共為期三年,2006財年主要是保持線性目標,結果是三洋實現了三年收縮目標的大部分任務,尤其是人員削減計劃被提前完成,資產縮減也是如火如荼,裁減了約30個部門,退出了DVD機以及卡式錄放映機業務;把年產100萬臺冰箱的工廠轉交給中國海爾公司;所擁有的三洋EPSON公司的股份全部轉讓給合資伙伴,從液晶顯示板市場徹底退出。資產縮減的同時,有著沉重利息負擔的負債得以減少。
在2007年3月31日結束的2006財年,是“中期管理計劃”定義的“重組”期,這一時期,三洋改革了專門的業務模型,在有關業務管理、采購、制造計術、物流與庫存控制方面,實現了集團范圍的優化。
“如果沒有假賬事件,三洋原定的2006財年的三大主題:‘加強公司治理’,‘鞏固全球發展’,‘進一步推進結構改革’算是取得了不錯的成果,2007財年的三洋有望進入增長期。”陸華說。
“所以,現在最關鍵的問題是:三洋假賬案一旦查證屬實,會在多大程度上打擊投資者的信心。
“我認為三洋不會變成安然,之所以這么說是因為日本人有很強的民族責任感,他們不愿把自己培養多年的民族企業打垮,美國人可能會選擇安然成為替罪羊,但日本人不會。”前述那位身在日本的朋友對記者說,“而且,已經給三洋注資的高盛、大和們,更不會輕易放棄。他們會努力提升投資者的信心,畢竟做了錯事的人已然離去。”
這份努力似乎在從丑聞披露當日就有表現,當時三洋股價跌幅最高曾達到28.8%,但收盤時即已拉回20.96%,而當年的安然可并不是這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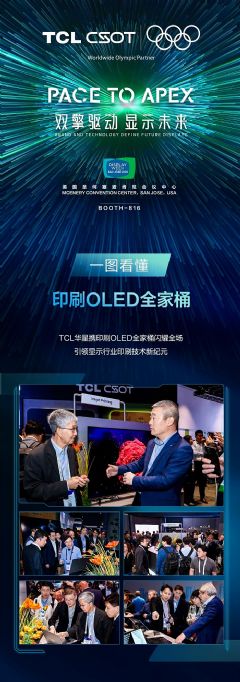











 康佳平板電視
康佳平板電視 創維平板電視
創維平板電視
 LG平板電視
LG平板電視 海信平板電視
海信平板電視 WAP手機版
WAP手機版 建議反饋
建議反饋 官方微博
官方微博 微信掃一掃
微信掃一掃 PjTime
PjTime